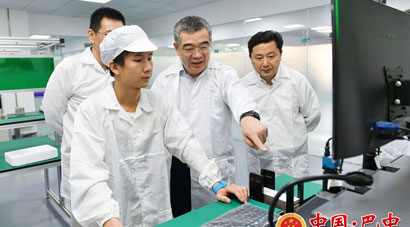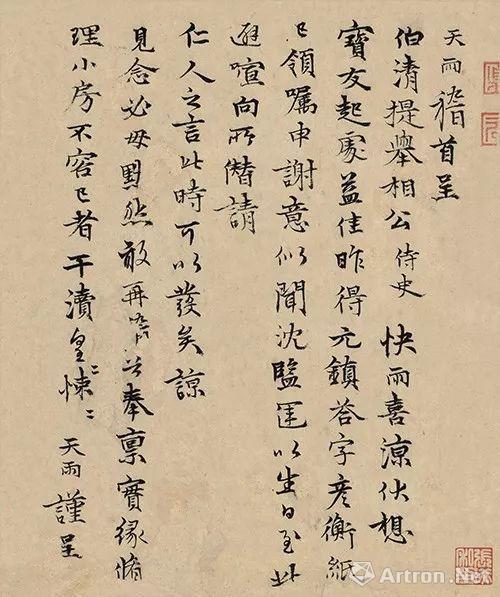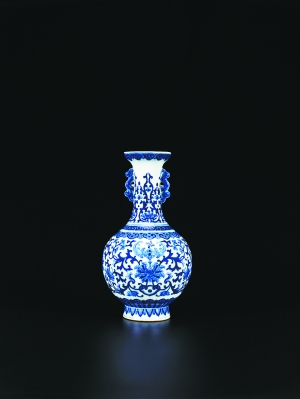我爱这充满人间气息的文字
鲁太光
应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邀请,我参加了2017年北京市基层群众文艺创作辅导活动,审读、评点了参评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审读完作品,与作者有了初步交流之后,有了一些想法,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原本的文学认识,颇有不吐不快之感。
正如此次活动主题所显示的,这次审读的稿件,作者极少是专业作家,绝大多数是基层文学爱好者,基于对生活和文学的真爱,使他们的作品洋溢着一种浓郁的人间气息。比如,郭玉祥的小小说《老夫老妻》,加上标点符号,一共1021个字,小说内容也简单,写一辈子受老杨打呼噜之苦的老伴儿,在老杨做了手术不打呼噜之后却遭遇了更大的困境——晚上听不见老杨打呼噜,她竟然更睡不好了,因为她总担心老杨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而为了缓释老伴儿的焦虑,好让她睡个安生觉,老杨就假装打呼噜,而且还偷偷打听有没有让人打呼噜的药……读了这样的小说,只能感慨真情自在人间。它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是打呼噜这件小事,还是这对老夫老妻相濡以沫的大半生,告诉了我们“家”的意义——情感和灵魂的港湾。
与这种热气蒸腾的现实感相呼应,这次审读的作品中另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就是乡愁。许福元的《香火地》写年近八十的得田老汉在孩子们都住上了楼房、日子越来越红火且诚心实意愿意为他养老的时候,竟然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要种荒废已久的香火地。更蹊跷的是,在这块香火地被征用盖楼前,老人家突然失踪了。经过全家、全村人寻找,最后,人们发现他竟然在这块香火地的中心地带、在青纱帐的保护下、在喇叭花的装点下永久地“睡着”了。其实,作者之所以带着我们寻找得田老汉,其实是想带着我们寻找那段人与土地、自然相依为命的岁月,是想带着我们寻找那段人与人之间相互扶助、彼此关爱的岁月,是想带着我们寻找乡土的真意,让我们感恩、善待乡土。
也有几位作者关注“命运”这个重要的文学主题。许震的《梨花殇》写的是一位普通农村女性张梨花中年丧夫后,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子女拉扯大,但子女长大成人后不仅不孝顺她,反而互相推诿扯皮,以致对簿公堂。一生本分的张梨花受不了这打击,以头抢石,自杀身亡,上演了一场催人泪下的“梨花殇”悲剧。梨花的悲剧不仅仅是个孝道问题、家庭问题,还与人心变异有关,因而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人性内涵,读了令人感到格外沉重。
这次审读的作品,不仅有生活,有现实,有内容,有“滋味”,而且在艺术上也可圈可点,王也丹的短篇小说《双面绣》、徐育伟的短篇小说《黑羊默克》、李强的中篇小说《我大爷是泰山》就是这样的好作品。《双面绣》构思相当精巧,以母亲收藏了一生的“双面绣”将“母亲”的生命故事和盘托出:原来,出嫁那天穿了一双“瞎鞋”(没有任何装饰的鞋)的母亲不仅不是一个拙妇,还是一位难得的巧妇,她之所以违背百年风俗,忍受一生冷遇,甚至被自己的丈夫不屑、嫌弃,是因为她在心底深深地埋藏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她之所以穿着一双“瞎鞋”出嫁,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这反抗,带给她的是无比沉重的代价——郁闷一生,憋屈而死。作家运笔相当宽厚、从容,小说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意义空间:我们一定要寻找、创造、呵护美丽的生活,再不要让它从我们心底、身边溜走。《黑羊默克》写的是黑羊默克与同类、敌类、人类的故事。作者表面上写的是羊,实际上写的是人,写的是人对各种桎梏的冲击,写的是人对各种压抑、异化的挑战,写的是反抗绝望,因此小说结尾当黑羊默克在枪声中倒下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灵魂,不仅是黑羊默克的灵魂,更是人的灵魂的崛起。《我大爷是泰山》小说内容极其简单,通过“我大爷”的故事提醒读者: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北京人”?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中国人”?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人”?一念及此,小说的境界便豁然开朗。
在我的视野中,这些年影响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培养作者的机构、活动、人员少,抢夺作者、作品的机构、活动、人员多。一位作家稍微有点成就和名声了,一大堆刊物和编辑就围上来约稿、要稿,某些地方作协也会想方设法将其签约为自己的“专业作家”,甚至影视剧公司、媒体也来凑热闹,或者淘金,或者赚取眼球。这样的现状,对作家个体,尤其是那些崭露头角,有一定名声、资源的写作者,或许是好事,毕竟机会多了,但对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却不见得有利。因为当资源、机会都集中到那几个“幸运儿”头上的时候,那些正在努力学习、艰难成长、需要扶一把的基层作家就乏人问津了。即便对那些“幸运儿”来说也不见得全是好事,如果他们缺乏定力,说不定就会成为下一个文学界的“仲永”。从这个角度看,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群众馆组织基层群众文艺创作辅导活动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这是在为中国文学培育土壤。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文学活动具有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文化需要、缓解社会矛盾的深刻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为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点赞,也希望北京的基层群众文艺创作活动、全国的基层文艺创作活动越办越好。